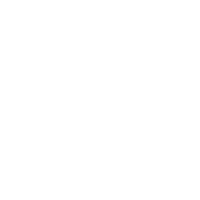劉海明在高一時被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其實,在此之前症狀早已顯現——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緒大起大落……由於對疾病沒有認知,劉海明一直沒去醫院,直到高一時病情越發嚴重,在學校心理老師的建議下才去了醫院精神科。確診後,劉海明休學了,此後的8年裡,他一直沒有回學校。
確診後的頭兩年,劉海明一直在吃藥治療,雖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卻沒有根本性改善。之後,他開始進行心理諮詢,其間換了幾個諮詢師,又開始自學後現代心理學,進行靜觀練習。一段時間後,病情終於開始好轉。去年,劉海明參加了高考,恢復了學業。
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劉海明在圓桌對話環節,分享了他的經歷,也與大學生姚靜秋、精神專科醫院醫師李潤之、心理師杜奕一起,探討後現代心理學在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健康問題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4月20日,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學生、老師、精神科醫生一起探討如何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辦方供圖
對疾病的反思
在最初的求醫過程中,劉海明一度感到迷茫和無助,他說,對於自己的疾病,自己和父母一開始都完全不瞭解,既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病,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能治好。而劉海明的第一位心理諮詢師也迴避與他和父母談論疾病,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對諮詢師的不信任。由於對病情認知不足,劉海明和父母經常因為病因發生衝突,劉海明覺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對此完全否認,於是雙方在互相“甩鍋”中發生了幾次相當嚴重的爭吵,導致劉海明病情一再復發,頻繁出現自殺念頭。
正在上大學的姚靜秋身邊也有幾個確診精神疾病的朋友,他們對她說,醫院精神科開的藥物只能緩解病理症狀,無法真正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而心理諮詢也沒有什麼幫助。心理諮詢師對自己沒有深入瞭解,每次都用同一套話術,提供不瞭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讓他們感到很無力,對繼續治療很抗拒。
對此,工作於某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的醫師李潤之也感到很無奈,他說,很多病人以及家屬對醫院有這樣一個心理預期,即醫院不應該只是看病吃藥,醫生還應給予一些心理安慰。然而現實是,這種期待是醫生目前無法滿足的,李潤之說,其實醫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工作壓力很大,不僅每天要看很多病人,還要保障醫療安全,因此精神科醫生除了在門診評估疾病之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病房管理上。除了工作壓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系統培訓過醫患心理干涉干與技術,我們是真的不會。”李潤之哭笑不得。
李潤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美國的醫療體系下,精神科醫生在規培期都要至少接受3個月到半年時間的心理治療培訓,而我國關於精神科的規培起步晚,處於探索階段。所以對心理學感興趣的醫生,大多數是靠自學。
回顧康復的經歷,劉海明感觸頗深。“在確診後的前幾年,我一直比較焦慮,擔心病情更加惡化,總想嘗試回學校上學,但實際上,當時的狀況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只要回到學校,病情就會反覆,只好再輟學回家。”
劉海明覺得,父母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好起來的。“讓我康復最關鍵的因素是,移除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執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劉海明說,“當我開始允許自己在家裡待著養病,不再急於恢復時,病情才真正開始好轉。”
劉海明從小到大的願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學,即使在生病後,明知這個願望變得很不現實,他也無法徹底放下這個執念。在更換了多位心理諮詢師之後,劉海明遇到了比較適合他的一位。“考北大這個念頭就像一隻八爪魚一樣,裹在我的腦子上。”每次和諮詢師說到這裡,他都會哭,“覺得自己特別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個人去怪罪,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最後發現這些都是自己建構出來的,所以只能怪自己。”
於是,心理諮詢師和他探討,考北大這件事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在心理諮詢師不斷幫助下,他的執念慢慢鬆動了。後來,劉海明開始學習後現代心理學,練習靜觀,慢慢地,他覺察到了自己的執念,而且能夠將其逐漸移除。他意識到,即使考上的學校不是北大,他也可以讀書,可以鍛鍊,這個新的可能性是他可以接受的,於是,他不再被之前的執念所束縛。慢慢地,他好了起來。
恢復健康後,劉海明經常反思,他感到,在康復過程中,父母的“不干涉干與”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議、期待、評價,這些看似比較中性的東西,其實對於生病的我來說,都是難以應對的壓力。”劉海明說,“生病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父母作為最親近的人,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其實父母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只要不讓自己的焦慮情緒影響孩子,不提要求、不設目標地接納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讓孩子減輕很多壓力。”
而在他看來,對於自己這種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學校如果能夠早發現、早識別,儘早轉移給更專業的人士治療,可能會恢復得更好。“其實我初三時就有很明顯的症狀了,到高中已經非常嚴重了,但老師、同學和家長都對這個疾病沒有認知。
關口前移的難點
為了保障學生的心理健康,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學校開展心理測評工作,以更好地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和需求。例如2021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到要做好學生心理健康測評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檔案。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強調規範心理健康監測,堅持預防為主、關口前移,定期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學校的心理測評工作還不能完全起到預期的效果。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學校在開展心理健康測評和心理健康普查時,有的班主任老師會要求班裡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控制在正常範圍之內,以免影響自己考核。所以,部分有心理問題的同學會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導致測評流於形式,也讓這些學生無法面對自己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有的同學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是因為對學校的心理老師很抗拒,覺得心理老師會把他的“秘密”告訴學校管理層,這會侵犯自己的隱私,而且學校管理層還會通知自己的父母,帶來麻煩。
在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師、杭州焦點解決學院心理危機干涉干與中心主任杜奕看來,學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的意義並不在於讓學生做心理測評問卷,而是對透過測評篩查出資料異常的同學進行訪談和干涉干與,而目前,在很多學校還沒有專業的人士來做這些事。
多年從事青少年厭學諮詢的杜奕和其團隊為很多學校提供了服務,她在工作中發現,對於篩查出有心理健康風險的學生,學校一般會批准無限期的病假,讓學生先回家休息好後再回校上課,然而卻很少有學生在回家之後能恢復心理健康。杜奕分析說,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跡,脫離了同伴關係,而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這些孩子回家後往往會染上網癮,天天玩遊戲,情況越來越糟。還有的孩子經過復學評估,被心理師認為情況暫時不亂,允許回校上課,然而這個時期的學生內心大多會有高敏感傾向,面對老師和考試時,哪怕一點微小的挫折與暗示,都容易再度情緒崩潰。杜奕說,康復期的學生經常會出現請假、無法完成作業、無法參加考試的情況,這會給老師的班級管理帶來相當大的挑戰。這些孩子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是重新適應學校生活,而不是努力提高學習成績。
事實上,青少年情緒障礙的評估比成年人要難得多。李潤之解釋說,像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等情緒障礙疾病,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臨床特徵差別較大,成年抑鬱症患者的表現可能是悲傷、情緒低落突出;而青少年表現出的可能是煩躁,易激惹,與家庭成員發生衝突,逃學等“青春期逆反”行為,醫生透過問診和查房也很難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與此同時,家長對醫院的預期也與現實有很大偏差。家長會以為,孩子住院了,情緒調好了,就可以回到學校復課,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他們認為醫生能把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都調整到與社會相容的完善狀態,“但其實,以醫院現有的資源,能把最基本的疾病評估做到完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李潤之說。
李潤之認為,實現精神專科醫院和學校的資源聯合很有必要。他說,精神治療最重要的環節是早期干涉干與和後期康復,而遺憾的是,目前病院所能做的只是疾病治療的環節。對於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早期識別、早期干涉干與,以及出院之後的康復,因為缺乏機制架構、在院期間能做到的干涉干與有限,需要聯合學校等多方面資源。
心理健康工作還可以做什麼
《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要開設心理健康相關課程,發揮課堂教學作用,結合大中小學生髮展需要,分層分類開展心理健康教授教養。
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高三下學期時她上過學校開設的心理健康課,一共有四節課,每月一節。因為是佔用晚自習時間,大家忙著複習備考,很少有人會去上課。最後一節課老師講的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自殘,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但那節課只有十幾個人參加。一個有心理問題的朋友對姚靜秋說,他期待的心理課不應該是這麼正式和教條。姚靜秋也覺得,“如果在心理課上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讓大家能夠互相瞭解,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並且在心理老師的指導下讓情緒得到疏浚溝通,也許效果會更好”。
姚靜秋曾經在大學裡組織開展過“自由擁抱”活動,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不認識的同學過來抱了她,流著眼淚對她說,自己這些天很悲傷,原本打算回宿舍自殘。但是看到了她之後,覺得可以對她說一些心裡話,自殘的念頭也沒有那麼強烈了。
姚靜秋認為,在大學開展心理互助活動會更加便利,因為在大學裡,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陌生人,也就更能放心傾訴心裡話,而且大學是一個素質更高的教育平臺,進入大學後,一個人在心靈上更加成熟,更能理智地看待心理問題。她建議,學校以社團的形式組建流動性的學生志願者組織,讓一些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並且擅長溝通的學生自發組織活動,活動不要過於正式,而是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有需求的同學可以自願參加,這樣他們更能在群體中獲得安慰。
在學校裡開展多年心理健康服務後,杜奕一直在反思,心理健康工作究竟是在做什麼?在對學校老師開展調研和培訓的過程中,杜奕發現,老師們最需要學習的其實是對心理問題的識別和應對,應該把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轉介給學校的心理老師,而不是把心理問題錯認是學生的品行問題。然而,讓老師們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再學習心理學專業知識,不免難免有些強人所難。不過杜奕發現,當自己跟他們講解如何把心性成長融入教書育人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中時,老師們很容易接受。“老師們可能更希望知道如何在現有教授教養制度下,透過改變自己,進而改變學生,所以這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方向。”杜奕說。
李潤之認為,精神專科與後現代心理學的結合對於精神科醫生也很有幫助。很多醫生對於心理學在臨床的運用很有熱情,但是對心理干涉干與目前的發展現狀並不瞭解,故而在臨床上很難施展,其實一些新興的治療流派,焦點解決療法、敘事療法、對話療法等後現代主義心理療法,早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心理治療室,在任何場景下,透過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起到心理干涉干與的效果,並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據他的觀察,病院裡也有不少醫生在經過短暫的學習後,便能在門診或者病房用上這些後現代心理學的方法。
翻開國內外精神病學的教材、專著,李潤之經常驚奇地發現,關於精神科醫生與病人進行訪談的過程,無一例外地要求醫生在評估患者病情的同時,兼具人文關懷,這也是成為一名優秀精神科醫師的必備素養。
“後現代心理學為臨床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實踐樣本,相信未來可以跟精神科完美融合。”李潤之說。
(應受訪者要求,劉海明、姚靜秋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劉海明在高一時被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其實,在此之前症狀早已顯現——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緒大起大落……由於對疾病沒有認知,劉海明一直沒去醫院,直到高一時病情越發嚴重,在學校心理老師的建議下才去了醫院精神科。確診後,劉海明休學了,此後的8年裡,他一直沒有回學校。
確診後的頭兩年,劉海明一直在吃藥治療,雖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卻沒有根本性改善。之後,他開始進行心理諮詢,其間換了幾個諮詢師,又開始自學後現代心理學,進行靜觀練習。一段時間後,病情終於開始好轉。去年,劉海明參加了高考,恢復了學業。
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劉海明在圓桌對話環節,分享了他的經歷,也與大學生姚靜秋、精神專科醫院醫師李潤之、心理師杜奕一起,探討後現代心理學在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健康問題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4月20日,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學生、老師、精神科醫生一起探討如何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辦方供圖
對疾病的反思
在最初的求醫過程中,劉海明一度感到迷茫和無助,他說,對於自己的疾病,自己和父母一開始都完全不瞭解,既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病,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能治好。而劉海明的第一位心理諮詢師也迴避與他和父母談論疾病,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對諮詢師的不信任。由於對病情認知不足,劉海明和父母經常因為病因發生衝突,劉海明覺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對此完全否認,於是雙方在互相“甩鍋”中發生了幾次相當嚴重的爭吵,導致劉海明病情一再復發,頻繁出現自殺念頭。
正在上大學的姚靜秋身邊也有幾個確診精神疾病的朋友,他們對她說,醫院精神科開的藥物只能緩解病理症狀,無法真正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而心理諮詢也沒有什麼幫助。心理諮詢師對自己沒有深入瞭解,每次都用同一套話術,提供不瞭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讓他們感到很無力,對繼續治療很抗拒。
對此,工作於某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的醫師李潤之也感到很無奈,他說,很多病人以及家屬對醫院有這樣一個心理預期,即醫院不應該只是看病吃藥,醫生還應給予一些心理安慰。然而現實是,這種期待是醫生目前無法滿足的,李潤之說,其實醫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工作壓力很大,不僅每天要看很多病人,還要保障醫療安全,因此精神科醫生除了在門診評估疾病之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病房管理上。除了工作壓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系統培訓過醫患心理干涉干與技術,我們是真的不會。”李潤之哭笑不得。
李潤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美國的醫療體系下,精神科醫生在規培期都要至少接受3個月到半年時間的心理治療培訓,而我國關於精神科的規培起步晚,處於探索階段。所以對心理學感興趣的醫生,大多數是靠自學。
回顧康復的經歷,劉海明感觸頗深。“在確診後的前幾年,我一直比較焦慮,擔心病情更加惡化,總想嘗試回學校上學,但實際上,當時的狀況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只要回到學校,病情就會反覆,只好再輟學回家。”
劉海明覺得,父母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好起來的。“讓我康復最關鍵的因素是,移除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執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劉海明說,“當我開始允許自己在家裡待著養病,不再急於恢復時,病情才真正開始好轉。”
劉海明從小到大的願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學,即使在生病後,明知這個願望變得很不現實,他也無法徹底放下這個執念。在更換了多位心理諮詢師之後,劉海明遇到了比較適合他的一位。“考北大這個念頭就像一隻八爪魚一樣,裹在我的腦子上。”每次和諮詢師說到這裡,他都會哭,“覺得自己特別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個人去怪罪,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最後發現這些都是自己建構出來的,所以只能怪自己。”
於是,心理諮詢師和他探討,考北大這件事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在心理諮詢師不斷幫助下,他的執念慢慢鬆動了。後來,劉海明開始學習後現代心理學,練習靜觀,慢慢地,他覺察到了自己的執念,而且能夠將其逐漸移除。他意識到,即使考上的學校不是北大,他也可以讀書,可以鍛鍊,這個新的可能性是他可以接受的,於是,他不再被之前的執念所束縛。慢慢地,他好了起來。
恢復健康後,劉海明經常反思,他感到,在康復過程中,父母的“不干涉干與”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議、期待、評價,這些看似比較中性的東西,其實對於生病的我來說,都是難以應對的壓力。”劉海明說,“生病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父母作為最親近的人,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其實父母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只要不讓自己的焦慮情緒影響孩子,不提要求、不設目標地接納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讓孩子減輕很多壓力。”
而在他看來,對於自己這種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學校如果能夠早發現、早識別,儘早轉移給更專業的人士治療,可能會恢復得更好。“其實我初三時就有很明顯的症狀了,到高中已經非常嚴重了,但老師、同學和家長都對這個疾病沒有認知。
關口前移的難點
為了保障學生的心理健康,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學校開展心理測評工作,以更好地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和需求。例如2021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到要做好學生心理健康測評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檔案。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強調規範心理健康監測,堅持預防為主、關口前移,定期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學校的心理測評工作還不能完全起到預期的效果。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學校在開展心理健康測評和心理健康普查時,有的班主任老師會要求班裡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控制在正常範圍之內,以免影響自己考核。所以,部分有心理問題的同學會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導致測評流於形式,也讓這些學生無法面對自己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有的同學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是因為對學校的心理老師很抗拒,覺得心理老師會把他的“秘密”告訴學校管理層,這會侵犯自己的隱私,而且學校管理層還會通知自己的父母,帶來麻煩。
在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師、杭州焦點解決學院心理危機干涉干與中心主任杜奕看來,學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的意義並不在於讓學生做心理測評問卷,而是對透過測評篩查出資料異常的同學進行訪談和干涉干與,而目前,在很多學校還沒有專業的人士來做這些事。
多年從事青少年厭學諮詢的杜奕和其團隊為很多學校提供了服務,她在工作中發現,對於篩查出有心理健康風險的學生,學校一般會批准無限期的病假,讓學生先回家休息好後再回校上課,然而卻很少有學生在回家之後能恢復心理健康。杜奕分析說,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跡,脫離了同伴關係,而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這些孩子回家後往往會染上網癮,天天玩遊戲,情況越來越糟。還有的孩子經過復學評估,被心理師認為情況暫時不亂,允許回校上課,然而這個時期的學生內心大多會有高敏感傾向,面對老師和考試時,哪怕一點微小的挫折與暗示,都容易再度情緒崩潰。杜奕說,康復期的學生經常會出現請假、無法完成作業、無法參加考試的情況,這會給老師的班級管理帶來相當大的挑戰。這些孩子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是重新適應學校生活,而不是努力提高學習成績。
事實上,青少年情緒障礙的評估比成年人要難得多。李潤之解釋說,像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等情緒障礙疾病,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臨床特徵差別較大,成年抑鬱症患者的表現可能是悲傷、情緒低落突出;而青少年表現出的可能是煩躁,易激惹,與家庭成員發生衝突,逃學等“青春期逆反”行為,醫生透過問診和查房也很難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與此同時,家長對醫院的預期也與現實有很大偏差。家長會以為,孩子住院了,情緒調好了,就可以回到學校復課,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他們認為醫生能把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都調整到與社會相容的完善狀態,“但其實,以醫院現有的資源,能把最基本的疾病評估做到完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李潤之說。
李潤之認為,實現精神專科醫院和學校的資源聯合很有必要。他說,精神治療最重要的環節是早期干涉干與和後期康復,而遺憾的是,目前病院所能做的只是疾病治療的環節。對於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早期識別、早期干涉干與,以及出院之後的康復,因為缺乏機制架構、在院期間能做到的干涉干與有限,需要聯合學校等多方面資源。
心理健康工作還可以做什麼
《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要開設心理健康相關課程,發揮課堂教學作用,結合大中小學生髮展需要,分層分類開展心理健康教授教養。
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高三下學期時她上過學校開設的心理健康課,一共有四節課,每月一節。因為是佔用晚自習時間,大家忙著複習備考,很少有人會去上課。最後一節課老師講的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自殘,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但那節課只有十幾個人參加。一個有心理問題的朋友對姚靜秋說,他期待的心理課不應該是這麼正式和教條。姚靜秋也覺得,“如果在心理課上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讓大家能夠互相瞭解,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並且在心理老師的指導下讓情緒得到疏浚溝通,也許效果會更好”。
姚靜秋曾經在大學裡組織開展過“自由擁抱”活動,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不認識的同學過來抱了她,流著眼淚對她說,自己這些天很悲傷,原本打算回宿舍自殘。但是看到了她之後,覺得可以對她說一些心裡話,自殘的念頭也沒有那麼強烈了。
姚靜秋認為,在大學開展心理互助活動會更加便利,因為在大學裡,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陌生人,也就更能放心傾訴心裡話,而且大學是一個素質更高的教育平臺,進入大學後,一個人在心靈上更加成熟,更能理智地看待心理問題。她建議,學校以社團的形式組建流動性的學生志願者組織,讓一些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並且擅長溝通的學生自發組織活動,活動不要過於正式,而是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有需求的同學可以自願參加,這樣他們更能在群體中獲得安慰。
在學校裡開展多年心理健康服務後,杜奕一直在反思,心理健康工作究竟是在做什麼?在對學校老師開展調研和培訓的過程中,杜奕發現,老師們最需要學習的其實是對心理問題的識別和應對,應該把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轉介給學校的心理老師,而不是把心理問題錯認是學生的品行問題。然而,讓老師們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再學習心理學專業知識,不免難免有些強人所難。不過杜奕發現,當自己跟他們講解如何把心性成長融入教書育人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中時,老師們很容易接受。“老師們可能更希望知道如何在現有教授教養制度下,透過改變自己,進而改變學生,所以這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方向。”杜奕說。
李潤之認為,精神專科與後現代心理學的結合對於精神科醫生也很有幫助。很多醫生對於心理學在臨床的運用很有熱情,但是對心理干涉干與目前的發展現狀並不瞭解,故而在臨床上很難施展,其實一些新興的治療流派,焦點解決療法、敘事療法、對話療法等後現代主義心理療法,早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心理治療室,在任何場景下,透過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起到心理干涉干與的效果,並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據他的觀察,病院裡也有不少醫生在經過短暫的學習後,便能在門診或者病房用上這些後現代心理學的方法。
翻開國內外精神病學的教材、專著,李潤之經常驚奇地發現,關於精神科醫生與病人進行訪談的過程,無一例外地要求醫生在評估患者病情的同時,兼具人文關懷,這也是成為一名優秀精神科醫師的必備素養。
“後現代心理學為臨床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實踐樣本,相信未來可以跟精神科完美融合。”李潤之說。
(應受訪者要求,劉海明、姚靜秋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劉海明在高一時被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其實,在此之前症狀早已顯現——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緒大起大落……由於對疾病沒有認知,劉海明一直沒去醫院,直到高一時病情越發嚴重,在學校心理老師的建議下才去了醫院精神科。確診後,劉海明休學了,此後的8年裡,他一直沒有回學校。
確診後的頭兩年,劉海明一直在吃藥治療,雖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卻沒有根本性改善。之後,他開始進行心理諮詢,其間換了幾個諮詢師,又開始自學後現代心理學,進行靜觀練習。一段時間後,病情終於開始好轉。去年,劉海明參加了高考,恢復了學業。
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劉海明在圓桌對話環節,分享了他的經歷,也與大學生姚靜秋、精神專科醫院醫師李潤之、心理師杜奕一起,探討後現代心理學在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健康問題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4月20日,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學生、老師、精神科醫生一起探討如何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辦方供圖
對疾病的反思
在最初的求醫過程中,劉海明一度感到迷茫和無助,他說,對於自己的疾病,自己和父母一開始都完全不瞭解,既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病,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能治好。而劉海明的第一位心理諮詢師也迴避與他和父母談論疾病,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對諮詢師的不信任。由於對病情認知不足,劉海明和父母經常因為病因發生衝突,劉海明覺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對此完全否認,於是雙方在互相“甩鍋”中發生了幾次相當嚴重的爭吵,導致劉海明病情一再復發,頻繁出現自殺念頭。
正在上大學的姚靜秋身邊也有幾個確診精神疾病的朋友,他們對她說,醫院精神科開的藥物只能緩解病理症狀,無法真正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而心理諮詢也沒有什麼幫助。心理諮詢師對自己沒有深入瞭解,每次都用同一套話術,提供不瞭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讓他們感到很無力,對繼續治療很抗拒。
對此,工作於某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的醫師李潤之也感到很無奈,他說,很多病人以及家屬對醫院有這樣一個心理預期,即醫院不應該只是看病吃藥,醫生還應給予一些心理安慰。然而現實是,這種期待是醫生目前無法滿足的,李潤之說,其實醫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工作壓力很大,不僅每天要看很多病人,還要保障醫療安全,因此精神科醫生除了在門診評估疾病之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病房管理上。除了工作壓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系統培訓過醫患心理干涉干與技術,我們是真的不會。”李潤之哭笑不得。
李潤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美國的醫療體系下,精神科醫生在規培期都要至少接受3個月到半年時間的心理治療培訓,而我國關於精神科的規培起步晚,處於探索階段。所以對心理學感興趣的醫生,大多數是靠自學。
回顧康復的經歷,劉海明感觸頗深。“在確診後的前幾年,我一直比較焦慮,擔心病情更加惡化,總想嘗試回學校上學,但實際上,當時的狀況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只要回到學校,病情就會反覆,只好再輟學回家。”
劉海明覺得,父母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好起來的。“讓我康復最關鍵的因素是,移除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執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劉海明說,“當我開始允許自己在家裡待著養病,不再急於恢復時,病情才真正開始好轉。”
劉海明從小到大的願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學,即使在生病後,明知這個願望變得很不現實,他也無法徹底放下這個執念。在更換了多位心理諮詢師之後,劉海明遇到了比較適合他的一位。“考北大這個念頭就像一隻八爪魚一樣,裹在我的腦子上。”每次和諮詢師說到這裡,他都會哭,“覺得自己特別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個人去怪罪,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最後發現這些都是自己建構出來的,所以只能怪自己。”
於是,心理諮詢師和他探討,考北大這件事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在心理諮詢師不斷幫助下,他的執念慢慢鬆動了。後來,劉海明開始學習後現代心理學,練習靜觀,慢慢地,他覺察到了自己的執念,而且能夠將其逐漸移除。他意識到,即使考上的學校不是北大,他也可以讀書,可以鍛鍊,這個新的可能性是他可以接受的,於是,他不再被之前的執念所束縛。慢慢地,他好了起來。
恢復健康後,劉海明經常反思,他感到,在康復過程中,父母的“不干涉干與”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議、期待、評價,這些看似比較中性的東西,其實對於生病的我來說,都是難以應對的壓力。”劉海明說,“生病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父母作為最親近的人,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其實父母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只要不讓自己的焦慮情緒影響孩子,不提要求、不設目標地接納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讓孩子減輕很多壓力。”
而在他看來,對於自己這種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學校如果能夠早發現、早識別,儘早轉移給更專業的人士治療,可能會恢復得更好。“其實我初三時就有很明顯的症狀了,到高中已經非常嚴重了,但老師、同學和家長都對這個疾病沒有認知。
關口前移的難點
為了保障學生的心理健康,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學校開展心理測評工作,以更好地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和需求。例如2021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到要做好學生心理健康測評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檔案。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強調規範心理健康監測,堅持預防為主、關口前移,定期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學校的心理測評工作還不能完全起到預期的效果。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學校在開展心理健康測評和心理健康普查時,有的班主任老師會要求班裡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控制在正常範圍之內,以免影響自己考核。所以,部分有心理問題的同學會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導致測評流於形式,也讓這些學生無法面對自己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有的同學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是因為對學校的心理老師很抗拒,覺得心理老師會把他的“秘密”告訴學校管理層,這會侵犯自己的隱私,而且學校管理層還會通知自己的父母,帶來麻煩。
在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師、杭州焦點解決學院心理危機干涉干與中心主任杜奕看來,學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的意義並不在於讓學生做心理測評問卷,而是對透過測評篩查出資料異常的同學進行訪談和干涉干與,而目前,在很多學校還沒有專業的人士來做這些事。
多年從事青少年厭學諮詢的杜奕和其團隊為很多學校提供了服務,她在工作中發現,對於篩查出有心理健康風險的學生,學校一般會批准無限期的病假,讓學生先回家休息好後再回校上課,然而卻很少有學生在回家之後能恢復心理健康。杜奕分析說,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跡,脫離了同伴關係,而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這些孩子回家後往往會染上網癮,天天玩遊戲,情況越來越糟。還有的孩子經過復學評估,被心理師認為情況暫時不亂,允許回校上課,然而這個時期的學生內心大多會有高敏感傾向,面對老師和考試時,哪怕一點微小的挫折與暗示,都容易再度情緒崩潰。杜奕說,康復期的學生經常會出現請假、無法完成作業、無法參加考試的情況,這會給老師的班級管理帶來相當大的挑戰。這些孩子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是重新適應學校生活,而不是努力提高學習成績。
事實上,青少年情緒障礙的評估比成年人要難得多。李潤之解釋說,像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等情緒障礙疾病,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臨床特徵差別較大,成年抑鬱症患者的表現可能是悲傷、情緒低落突出;而青少年表現出的可能是煩躁,易激惹,與家庭成員發生衝突,逃學等“青春期逆反”行為,醫生透過問診和查房也很難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與此同時,家長對醫院的預期也與現實有很大偏差。家長會以為,孩子住院了,情緒調好了,就可以回到學校復課,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他們認為醫生能把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都調整到與社會相容的完善狀態,“但其實,以醫院現有的資源,能把最基本的疾病評估做到完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李潤之說。
李潤之認為,實現精神專科醫院和學校的資源聯合很有必要。他說,精神治療最重要的環節是早期干涉干與和後期康復,而遺憾的是,目前病院所能做的只是疾病治療的環節。對於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早期識別、早期干涉干與,以及出院之後的康復,因為缺乏機制架構、在院期間能做到的干涉干與有限,需要聯合學校等多方面資源。
心理健康工作還可以做什麼
《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要開設心理健康相關課程,發揮課堂教學作用,結合大中小學生髮展需要,分層分類開展心理健康教授教養。
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高三下學期時她上過學校開設的心理健康課,一共有四節課,每月一節。因為是佔用晚自習時間,大家忙著複習備考,很少有人會去上課。最後一節課老師講的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自殘,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但那節課只有十幾個人參加。一個有心理問題的朋友對姚靜秋說,他期待的心理課不應該是這麼正式和教條。姚靜秋也覺得,“如果在心理課上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讓大家能夠互相瞭解,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並且在心理老師的指導下讓情緒得到疏浚溝通,也許效果會更好”。
姚靜秋曾經在大學裡組織開展過“自由擁抱”活動,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不認識的同學過來抱了她,流著眼淚對她說,自己這些天很悲傷,原本打算回宿舍自殘。但是看到了她之後,覺得可以對她說一些心裡話,自殘的念頭也沒有那麼強烈了。
姚靜秋認為,在大學開展心理互助活動會更加便利,因為在大學裡,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陌生人,也就更能放心傾訴心裡話,而且大學是一個素質更高的教育平臺,進入大學後,一個人在心靈上更加成熟,更能理智地看待心理問題。她建議,學校以社團的形式組建流動性的學生志願者組織,讓一些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並且擅長溝通的學生自發組織活動,活動不要過於正式,而是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有需求的同學可以自願參加,這樣他們更能在群體中獲得安慰。
在學校裡開展多年心理健康服務後,杜奕一直在反思,心理健康工作究竟是在做什麼?在對學校老師開展調研和培訓的過程中,杜奕發現,老師們最需要學習的其實是對心理問題的識別和應對,應該把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轉介給學校的心理老師,而不是把心理問題錯認是學生的品行問題。然而,讓老師們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再學習心理學專業知識,不免難免有些強人所難。不過杜奕發現,當自己跟他們講解如何把心性成長融入教書育人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中時,老師們很容易接受。“老師們可能更希望知道如何在現有教授教養制度下,透過改變自己,進而改變學生,所以這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方向。”杜奕說。
李潤之認為,精神專科與後現代心理學的結合對於精神科醫生也很有幫助。很多醫生對於心理學在臨床的運用很有熱情,但是對心理干涉干與目前的發展現狀並不瞭解,故而在臨床上很難施展,其實一些新興的治療流派,焦點解決療法、敘事療法、對話療法等後現代主義心理療法,早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心理治療室,在任何場景下,透過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起到心理干涉干與的效果,並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據他的觀察,病院裡也有不少醫生在經過短暫的學習後,便能在門診或者病房用上這些後現代心理學的方法。
翻開國內外精神病學的教材、專著,李潤之經常驚奇地發現,關於精神科醫生與病人進行訪談的過程,無一例外地要求醫生在評估患者病情的同時,兼具人文關懷,這也是成為一名優秀精神科醫師的必備素養。
“後現代心理學為臨床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實踐樣本,相信未來可以跟精神科完美融合。”李潤之說。
(應受訪者要求,劉海明、姚靜秋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劉海明在高一時被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其實,在此之前症狀早已顯現——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緒大起大落……由於對疾病沒有認知,劉海明一直沒去醫院,直到高一時病情越發嚴重,在學校心理老師的建議下才去了醫院精神科。確診後,劉海明休學了,此後的8年裡,他一直沒有回學校。
確診後的頭兩年,劉海明一直在吃藥治療,雖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卻沒有根本性改善。之後,他開始進行心理諮詢,其間換了幾個諮詢師,又開始自學後現代心理學,進行靜觀練習。一段時間後,病情終於開始好轉。去年,劉海明參加了高考,恢復了學業。
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劉海明在圓桌對話環節,分享了他的經歷,也與大學生姚靜秋、精神專科醫院醫師李潤之、心理師杜奕一起,探討後現代心理學在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健康問題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4月20日,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學生、老師、精神科醫生一起探討如何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辦方供圖
對疾病的反思
在最初的求醫過程中,劉海明一度感到迷茫和無助,他說,對於自己的疾病,自己和父母一開始都完全不瞭解,既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病,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能治好。而劉海明的第一位心理諮詢師也迴避與他和父母談論疾病,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對諮詢師的不信任。由於對病情認知不足,劉海明和父母經常因為病因發生衝突,劉海明覺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對此完全否認,於是雙方在互相“甩鍋”中發生了幾次相當嚴重的爭吵,導致劉海明病情一再復發,頻繁出現自殺念頭。
正在上大學的姚靜秋身邊也有幾個確診精神疾病的朋友,他們對她說,醫院精神科開的藥物只能緩解病理症狀,無法真正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而心理諮詢也沒有什麼幫助。心理諮詢師對自己沒有深入瞭解,每次都用同一套話術,提供不瞭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讓他們感到很無力,對繼續治療很抗拒。
對此,工作於某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的醫師李潤之也感到很無奈,他說,很多病人以及家屬對醫院有這樣一個心理預期,即醫院不應該只是看病吃藥,醫生還應給予一些心理安慰。然而現實是,這種期待是醫生目前無法滿足的,李潤之說,其實醫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工作壓力很大,不僅每天要看很多病人,還要保障醫療安全,因此精神科醫生除了在門診評估疾病之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病房管理上。除了工作壓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系統培訓過醫患心理干涉干與技術,我們是真的不會。”李潤之哭笑不得。
李潤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美國的醫療體系下,精神科醫生在規培期都要至少接受3個月到半年時間的心理治療培訓,而我國關於精神科的規培起步晚,處於探索階段。所以對心理學感興趣的醫生,大多數是靠自學。
回顧康復的經歷,劉海明感觸頗深。“在確診後的前幾年,我一直比較焦慮,擔心病情更加惡化,總想嘗試回學校上學,但實際上,當時的狀況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只要回到學校,病情就會反覆,只好再輟學回家。”
劉海明覺得,父母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好起來的。“讓我康復最關鍵的因素是,移除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執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劉海明說,“當我開始允許自己在家裡待著養病,不再急於恢復時,病情才真正開始好轉。”
劉海明從小到大的願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學,即使在生病後,明知這個願望變得很不現實,他也無法徹底放下這個執念。在更換了多位心理諮詢師之後,劉海明遇到了比較適合他的一位。“考北大這個念頭就像一隻八爪魚一樣,裹在我的腦子上。”每次和諮詢師說到這裡,他都會哭,“覺得自己特別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個人去怪罪,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最後發現這些都是自己建構出來的,所以只能怪自己。”
於是,心理諮詢師和他探討,考北大這件事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在心理諮詢師不斷幫助下,他的執念慢慢鬆動了。後來,劉海明開始學習後現代心理學,練習靜觀,慢慢地,他覺察到了自己的執念,而且能夠將其逐漸移除。他意識到,即使考上的學校不是北大,他也可以讀書,可以鍛鍊,這個新的可能性是他可以接受的,於是,他不再被之前的執念所束縛。慢慢地,他好了起來。
恢復健康後,劉海明經常反思,他感到,在康復過程中,父母的“不干涉干與”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議、期待、評價,這些看似比較中性的東西,其實對於生病的我來說,都是難以應對的壓力。”劉海明說,“生病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父母作為最親近的人,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其實父母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只要不讓自己的焦慮情緒影響孩子,不提要求、不設目標地接納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讓孩子減輕很多壓力。”
而在他看來,對於自己這種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學校如果能夠早發現、早識別,儘早轉移給更專業的人士治療,可能會恢復得更好。“其實我初三時就有很明顯的症狀了,到高中已經非常嚴重了,但老師、同學和家長都對這個疾病沒有認知。
關口前移的難點
為了保障學生的心理健康,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學校開展心理測評工作,以更好地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和需求。例如2021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到要做好學生心理健康測評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檔案。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強調規範心理健康監測,堅持預防為主、關口前移,定期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學校的心理測評工作還不能完全起到預期的效果。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學校在開展心理健康測評和心理健康普查時,有的班主任老師會要求班裡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控制在正常範圍之內,以免影響自己考核。所以,部分有心理問題的同學會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導致測評流於形式,也讓這些學生無法面對自己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有的同學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是因為對學校的心理老師很抗拒,覺得心理老師會把他的“秘密”告訴學校管理層,這會侵犯自己的隱私,而且學校管理層還會通知自己的父母,帶來麻煩。
在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師、杭州焦點解決學院心理危機干涉干與中心主任杜奕看來,學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的意義並不在於讓學生做心理測評問卷,而是對透過測評篩查出資料異常的同學進行訪談和干涉干與,而目前,在很多學校還沒有專業的人士來做這些事。
多年從事青少年厭學諮詢的杜奕和其團隊為很多學校提供了服務,她在工作中發現,對於篩查出有心理健康風險的學生,學校一般會批准無限期的病假,讓學生先回家休息好後再回校上課,然而卻很少有學生在回家之後能恢復心理健康。杜奕分析說,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跡,脫離了同伴關係,而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這些孩子回家後往往會染上網癮,天天玩遊戲,情況越來越糟。還有的孩子經過復學評估,被心理師認為情況暫時不亂,允許回校上課,然而這個時期的學生內心大多會有高敏感傾向,面對老師和考試時,哪怕一點微小的挫折與暗示,都容易再度情緒崩潰。杜奕說,康復期的學生經常會出現請假、無法完成作業、無法參加考試的情況,這會給老師的班級管理帶來相當大的挑戰。這些孩子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是重新適應學校生活,而不是努力提高學習成績。
事實上,青少年情緒障礙的評估比成年人要難得多。李潤之解釋說,像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等情緒障礙疾病,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臨床特徵差別較大,成年抑鬱症患者的表現可能是悲傷、情緒低落突出;而青少年表現出的可能是煩躁,易激惹,與家庭成員發生衝突,逃學等“青春期逆反”行為,醫生透過問診和查房也很難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與此同時,家長對醫院的預期也與現實有很大偏差。家長會以為,孩子住院了,情緒調好了,就可以回到學校復課,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他們認為醫生能把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都調整到與社會相容的完善狀態,“但其實,以醫院現有的資源,能把最基本的疾病評估做到完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李潤之說。
李潤之認為,實現精神專科醫院和學校的資源聯合很有必要。他說,精神治療最重要的環節是早期干涉干與和後期康復,而遺憾的是,目前病院所能做的只是疾病治療的環節。對於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早期識別、早期干涉干與,以及出院之後的康復,因為缺乏機制架構、在院期間能做到的干涉干與有限,需要聯合學校等多方面資源。
心理健康工作還可以做什麼
《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要開設心理健康相關課程,發揮課堂教學作用,結合大中小學生髮展需要,分層分類開展心理健康教授教養。
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高三下學期時她上過學校開設的心理健康課,一共有四節課,每月一節。因為是佔用晚自習時間,大家忙著複習備考,很少有人會去上課。最後一節課老師講的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自殘,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但那節課只有十幾個人參加。一個有心理問題的朋友對姚靜秋說,他期待的心理課不應該是這麼正式和教條。姚靜秋也覺得,“如果在心理課上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讓大家能夠互相瞭解,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並且在心理老師的指導下讓情緒得到疏浚溝通,也許效果會更好”。
姚靜秋曾經在大學裡組織開展過“自由擁抱”活動,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不認識的同學過來抱了她,流著眼淚對她說,自己這些天很悲傷,原本打算回宿舍自殘。但是看到了她之後,覺得可以對她說一些心裡話,自殘的念頭也沒有那麼強烈了。
姚靜秋認為,在大學開展心理互助活動會更加便利,因為在大學裡,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陌生人,也就更能放心傾訴心裡話,而且大學是一個素質更高的教育平臺,進入大學後,一個人在心靈上更加成熟,更能理智地看待心理問題。她建議,學校以社團的形式組建流動性的學生志願者組織,讓一些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並且擅長溝通的學生自發組織活動,活動不要過於正式,而是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有需求的同學可以自願參加,這樣他們更能在群體中獲得安慰。
在學校裡開展多年心理健康服務後,杜奕一直在反思,心理健康工作究竟是在做什麼?在對學校老師開展調研和培訓的過程中,杜奕發現,老師們最需要學習的其實是對心理問題的識別和應對,應該把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轉介給學校的心理老師,而不是把心理問題錯認是學生的品行問題。然而,讓老師們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再學習心理學專業知識,不免難免有些強人所難。不過杜奕發現,當自己跟他們講解如何把心性成長融入教書育人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中時,老師們很容易接受。“老師們可能更希望知道如何在現有教授教養制度下,透過改變自己,進而改變學生,所以這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方向。”杜奕說。
李潤之認為,精神專科與後現代心理學的結合對於精神科醫生也很有幫助。很多醫生對於心理學在臨床的運用很有熱情,但是對心理干涉干與目前的發展現狀並不瞭解,故而在臨床上很難施展,其實一些新興的治療流派,焦點解決療法、敘事療法、對話療法等後現代主義心理療法,早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心理治療室,在任何場景下,透過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起到心理干涉干與的效果,並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據他的觀察,病院裡也有不少醫生在經過短暫的學習後,便能在門診或者病房用上這些後現代心理學的方法。
翻開國內外精神病學的教材、專著,李潤之經常驚奇地發現,關於精神科醫生與病人進行訪談的過程,無一例外地要求醫生在評估患者病情的同時,兼具人文關懷,這也是成為一名優秀精神科醫師的必備素養。
“後現代心理學為臨床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實踐樣本,相信未來可以跟精神科完美融合。”李潤之說。
(應受訪者要求,劉海明、姚靜秋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劉海明在高一時被確診了雙相情感障礙。其實,在此之前症狀早已顯現——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緒大起大落……由於對疾病沒有認知,劉海明一直沒去醫院,直到高一時病情越發嚴重,在學校心理老師的建議下才去了醫院精神科。確診後,劉海明休學了,此後的8年裡,他一直沒有回學校。
確診後的頭兩年,劉海明一直在吃藥治療,雖然病情得到了控制,卻沒有根本性改善。之後,他開始進行心理諮詢,其間換了幾個諮詢師,又開始自學後現代心理學,進行靜觀練習。一段時間後,病情終於開始好轉。去年,劉海明參加了高考,恢復了學業。
4月20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劉海明在圓桌對話環節,分享了他的經歷,也與大學生姚靜秋、精神專科醫院醫師李潤之、心理師杜奕一起,探討後現代心理學在青少年遇到的心理健康問題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4月20日,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青少年人格與健康促進中心和中青線上主辦、三智書院和晨星學堂承辦的第八屆優秀傳統文化與後現代心理學學術交流大會上,學生、老師、精神科醫生一起探討如何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主辦方供圖
對疾病的反思
在最初的求醫過程中,劉海明一度感到迷茫和無助,他說,對於自己的疾病,自己和父母一開始都完全不瞭解,既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病,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能治好。而劉海明的第一位心理諮詢師也迴避與他和父母談論疾病,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對諮詢師的不信任。由於對病情認知不足,劉海明和父母經常因為病因發生衝突,劉海明覺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對此完全否認,於是雙方在互相“甩鍋”中發生了幾次相當嚴重的爭吵,導致劉海明病情一再復發,頻繁出現自殺念頭。
正在上大學的姚靜秋身邊也有幾個確診精神疾病的朋友,他們對她說,醫院精神科開的藥物只能緩解病理症狀,無法真正解決自己的心理問題,而心理諮詢也沒有什麼幫助。心理諮詢師對自己沒有深入瞭解,每次都用同一套話術,提供不瞭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讓他們感到很無力,對繼續治療很抗拒。
對此,工作於某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的醫師李潤之也感到很無奈,他說,很多病人以及家屬對醫院有這樣一個心理預期,即醫院不應該只是看病吃藥,醫生還應給予一些心理安慰。然而現實是,這種期待是醫生目前無法滿足的,李潤之說,其實醫生能做的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為醫生的工作壓力很大,不僅每天要看很多病人,還要保障醫療安全,因此精神科醫生除了在門診評估疾病之外,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病房管理上。除了工作壓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系統培訓過醫患心理干涉干與技術,我們是真的不會。”李潤之哭笑不得。
李潤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美國的醫療體系下,精神科醫生在規培期都要至少接受3個月到半年時間的心理治療培訓,而我國關於精神科的規培起步晚,處於探索階段。所以對心理學感興趣的醫生,大多數是靠自學。
回顧康復的經歷,劉海明感觸頗深。“在確診後的前幾年,我一直比較焦慮,擔心病情更加惡化,總想嘗試回學校上學,但實際上,當時的狀況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只要回到學校,病情就會反覆,只好再輟學回家。”
劉海明覺得,父母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好起來的。“讓我康復最關鍵的因素是,移除了過去長期存在的執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劉海明說,“當我開始允許自己在家裡待著養病,不再急於恢復時,病情才真正開始好轉。”
劉海明從小到大的願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學,即使在生病後,明知這個願望變得很不現實,他也無法徹底放下這個執念。在更換了多位心理諮詢師之後,劉海明遇到了比較適合他的一位。“考北大這個念頭就像一隻八爪魚一樣,裹在我的腦子上。”每次和諮詢師說到這裡,他都會哭,“覺得自己特別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個人去怪罪,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最後發現這些都是自己建構出來的,所以只能怪自己。”
於是,心理諮詢師和他探討,考北大這件事對他來說究竟有什麼意義。在心理諮詢師不斷幫助下,他的執念慢慢鬆動了。後來,劉海明開始學習後現代心理學,練習靜觀,慢慢地,他覺察到了自己的執念,而且能夠將其逐漸移除。他意識到,即使考上的學校不是北大,他也可以讀書,可以鍛鍊,這個新的可能性是他可以接受的,於是,他不再被之前的執念所束縛。慢慢地,他好了起來。
恢復健康後,劉海明經常反思,他感到,在康復過程中,父母的“不干涉干與”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議、期待、評價,這些看似比較中性的東西,其實對於生病的我來說,都是難以應對的壓力。”劉海明說,“生病的時候,人會變得特別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而父母作為最親近的人,帶來的影響是最大的。其實父母不需要特別做什麼,只要不讓自己的焦慮情緒影響孩子,不提要求、不設目標地接納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讓孩子減輕很多壓力。”
而在他看來,對於自己這種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學校如果能夠早發現、早識別,儘早轉移給更專業的人士治療,可能會恢復得更好。“其實我初三時就有很明顯的症狀了,到高中已經非常嚴重了,但老師、同學和家長都對這個疾病沒有認知。
關口前移的難點
為了保障學生的心理健康,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鼓勵學校開展心理測評工作,以更好地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態和需求。例如2021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到要做好學生心理健康測評工作,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檔案。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強調規範心理健康監測,堅持預防為主、關口前移,定期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學校的心理測評工作還不能完全起到預期的效果。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學校在開展心理健康測評和心理健康普查時,有的班主任老師會要求班裡學生心理問題檢出率控制在正常範圍之內,以免影響自己考核。所以,部分有心理問題的同學會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導致測評流於形式,也讓這些學生無法面對自己的心理問題。另一方面,有的同學隱瞞自己的心理狀況是因為對學校的心理老師很抗拒,覺得心理老師會把他的“秘密”告訴學校管理層,這會侵犯自己的隱私,而且學校管理層還會通知自己的父母,帶來麻煩。
在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師、杭州焦點解決學院心理危機干涉干與中心主任杜奕看來,學校開展學生心理健康測評的意義並不在於讓學生做心理測評問卷,而是對透過測評篩查出資料異常的同學進行訪談和干涉干與,而目前,在很多學校還沒有專業的人士來做這些事。
多年從事青少年厭學諮詢的杜奕和其團隊為很多學校提供了服務,她在工作中發現,對於篩查出有心理健康風險的學生,學校一般會批准無限期的病假,讓學生先回家休息好後再回校上課,然而卻很少有學生在回家之後能恢復心理健康。杜奕分析說,這是因為他們脫離了正常的生活軌跡,脫離了同伴關係,而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非常不利。這些孩子回家後往往會染上網癮,天天玩遊戲,情況越來越糟。還有的孩子經過復學評估,被心理師認為情況暫時不亂,允許回校上課,然而這個時期的學生內心大多會有高敏感傾向,面對老師和考試時,哪怕一點微小的挫折與暗示,都容易再度情緒崩潰。杜奕說,康復期的學生經常會出現請假、無法完成作業、無法參加考試的情況,這會給老師的班級管理帶來相當大的挑戰。這些孩子們的最高優先順序應該是重新適應學校生活,而不是努力提高學習成績。
事實上,青少年情緒障礙的評估比成年人要難得多。李潤之解釋說,像抑鬱症、雙相情感障礙等情緒障礙疾病,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臨床特徵差別較大,成年抑鬱症患者的表現可能是悲傷、情緒低落突出;而青少年表現出的可能是煩躁,易激惹,與家庭成員發生衝突,逃學等“青春期逆反”行為,醫生透過問診和查房也很難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與此同時,家長對醫院的預期也與現實有很大偏差。家長會以為,孩子住院了,情緒調好了,就可以回到學校復課,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他們認為醫生能把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都調整到與社會相容的完善狀態,“但其實,以醫院現有的資源,能把最基本的疾病評估做到完善,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李潤之說。
李潤之認為,實現精神專科醫院和學校的資源聯合很有必要。他說,精神治療最重要的環節是早期干涉干與和後期康復,而遺憾的是,目前病院所能做的只是疾病治療的環節。對於青少年精神障礙的早期識別、早期干涉干與,以及出院之後的康復,因為缺乏機制架構、在院期間能做到的干涉干與有限,需要聯合學校等多方面資源。
心理健康工作還可以做什麼
《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明確提出,要開設心理健康相關課程,發揮課堂教學作用,結合大中小學生髮展需要,分層分類開展心理健康教授教養。
姚靜秋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高三下學期時她上過學校開設的心理健康課,一共有四節課,每月一節。因為是佔用晚自習時間,大家忙著複習備考,很少有人會去上課。最後一節課老師講的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自殘,要尋求精神科醫生的幫助。但那節課只有十幾個人參加。一個有心理問題的朋友對姚靜秋說,他期待的心理課不應該是這麼正式和教條。姚靜秋也覺得,“如果在心理課上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讓大家能夠互相瞭解,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並且在心理老師的指導下讓情緒得到疏浚溝通,也許效果會更好”。
姚靜秋曾經在大學裡組織開展過“自由擁抱”活動,獲得了不錯的反響。她清楚地記得有一個不認識的同學過來抱了她,流著眼淚對她說,自己這些天很悲傷,原本打算回宿舍自殘。但是看到了她之後,覺得可以對她說一些心裡話,自殘的念頭也沒有那麼強烈了。
姚靜秋認為,在大學開展心理互助活動會更加便利,因為在大學裡,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彼此都是陌生人,也就更能放心傾訴心裡話,而且大學是一個素質更高的教育平臺,進入大學後,一個人在心靈上更加成熟,更能理智地看待心理問題。她建議,學校以社團的形式組建流動性的學生志願者組織,讓一些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並且擅長溝通的學生自發組織活動,活動不要過於正式,而是設定一些遊戲環節和分享環節,有需求的同學可以自願參加,這樣他們更能在群體中獲得安慰。
在學校裡開展多年心理健康服務後,杜奕一直在反思,心理健康工作究竟是在做什麼?在對學校老師開展調研和培訓的過程中,杜奕發現,老師們最需要學習的其實是對心理問題的識別和應對,應該把有心理問題的學生轉介給學校的心理老師,而不是把心理問題錯認是學生的品行問題。然而,讓老師們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再學習心理學專業知識,不免難免有些強人所難。不過杜奕發現,當自己跟他們講解如何把心性成長融入教書育人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中時,老師們很容易接受。“老師們可能更希望知道如何在現有教授教養制度下,透過改變自己,進而改變學生,所以這可能是未來值得探索的方向。”杜奕說。
李潤之認為,精神專科與後現代心理學的結合對於精神科醫生也很有幫助。很多醫生對於心理學在臨床的運用很有熱情,但是對心理干涉干與目前的發展現狀並不瞭解,故而在臨床上很難施展,其實一些新興的治療流派,焦點解決療法、敘事療法、對話療法等後現代主義心理療法,早已經走出了傳統的心理治療室,在任何場景下,透過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起到心理干涉干與的效果,並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醫患關係。據他的觀察,病院裡也有不少醫生在經過短暫的學習後,便能在門診或者病房用上這些後現代心理學的方法。
翻開國內外精神病學的教材、專著,李潤之經常驚奇地發現,關於精神科醫生與病人進行訪談的過程,無一例外地要求醫生在評估患者病情的同時,兼具人文關懷,這也是成為一名優秀精神科醫師的必備素養。
“後現代心理學為臨床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實踐樣本,相信未來可以跟精神科完美融合。”李潤之說。
(應受訪者要求,劉海明、姚靜秋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